第176期主持人|王鹏凯
整理|实习记者 覃瑜曦
日前,《卿本著者》一书因译后记中的一些表达而引发争议,随后出版方宣布下架此书。在本次事件中,有关男译者是否可以翻译女性主义著作的争论持续发酵,有读者由此出发梳理了过往男译者作品中潜在的男性凝视和文字厌女,也有出版方推出了全女译者书单,那么,翻译乃至文艺创作是否与性别身份有关?
这样的问题不只关乎性别,而是可以延伸到更广泛的创作中。本月上映的听障题材电影《独一无二》(中国版《健听女孩》)中,导演也选择由健全演员出演残障者,这回到了文艺创作中长久存在的问题:是否只有特定群体拥有对话题的解释合法性?类似的问题还有,男导演能不能拍好女性形象,健全人能不能演好残障电影,中产能不能写出底层生活,等等。

在身份政治愈演愈烈的当下,我们如何理解文艺创作中的“身份”,它又如何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生活?
01 为何女性叙事由男性书写

王鹏凯:我先简单复述一下《卿本著者》事件的争议。有读者认为译者将一些原文里相对中性的词汇译得有男凝色彩,比如将“adolescence”(青春期)、“puberty”(青春期)”译为“妙龄”、“含苞待放”,“malleable”(易受影响的)译为“调教”等。但随后也有读者认为,这种处理是为了符合上下文语境,此处原本就是在写中国古代父权逻辑中女性角色物化与驯化。还有读者则表示,这一问题在其它翻译类作品中亦有体现,比如“old maid”经常被翻译成“老处女”,女性被称为“骚货”。我回想了一下,过去的确有不少重要的女性主义作品是由男译者翻译的,但这件事在当下成为了被争论的议题,这其中是否揭示了社会心态的转变?文艺创作是否真的与性别有关?
徐鲁青:我觉得关键还要看角色形象是什么样的,假如作品中的男性角色本身就不尊重女性,那可能“骚货”“调教”就是本意。一个作家是不是一定要亲身经历某种身份或是某种真实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呢?要是我们要求每个身份都对应的话,那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根本没法写出来,好作品的创作应该不仅是对自身真实经验的复刻,也需要作者对其他身份有理解。有些男作家无法真正理解和体察女性的所思所想,无法真正地共情、代入到女性之中,这使他没有办法写出好的女性形象,而不是他没有办法说出正确的女性主义的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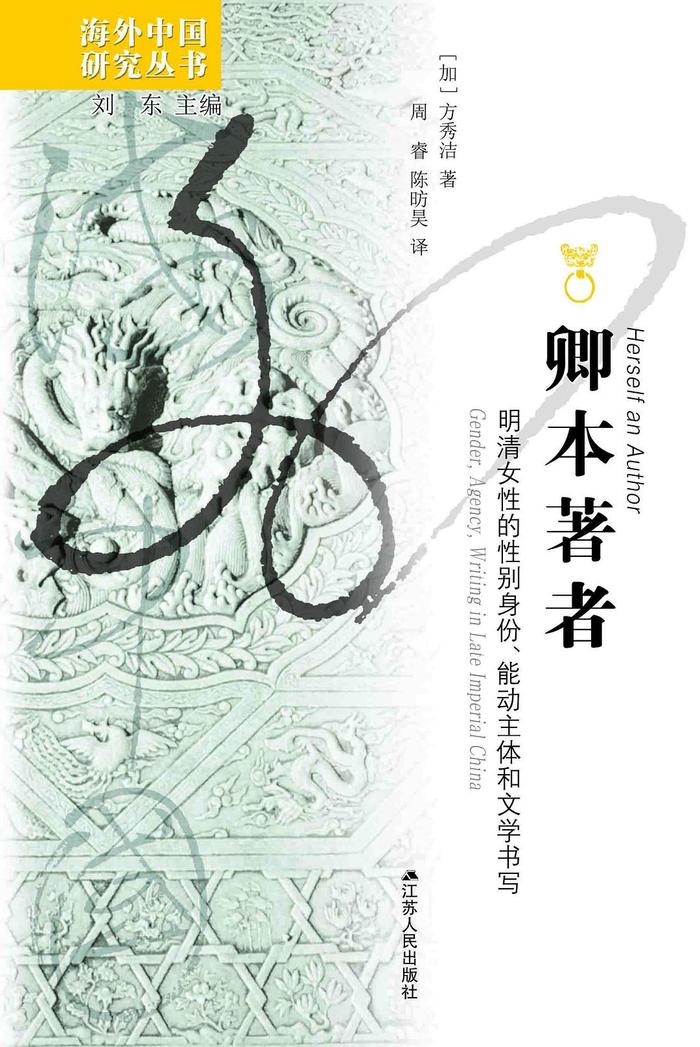
[加] 方秀洁 著 周睿 陈昉昊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2
王鹏凯:“写作的权利”这个问题很关键。在过去几百年的文学史/思想史中,有关女性的许多重要概念或命题好像都是男性提出的,例如易卜生写的娜拉出走,鲁迅写的娜拉走后怎样。
前段时间我读到日裔美国作家凯蒂·北村(Katie Kitamura)的一篇访谈,当被问到为什么前两本书写男主角,后三本书转向写女主角时,她的回答大意是:在文学界书写男性角色总是更容易的,你接受的几乎所有文学史和创意写作训练都在教你写男人,而写女人更难,写作训练本身也是性别结构。
还有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性形象——包法利夫人。去年《纽约客》有一篇文章写到,福楼拜最知名的那句“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其实是他对一位女性友人说的,她叫艾米丽·博斯凯(Amélie Bosquet),是法国当时的一位激进女性主义者,她和另一位福楼拜当时的情人、作家路易丝·柯莱(Louise Colet)被认为启发了福楼拜的写作,在当时,博斯凯也写作了另一本小说,剧情和人物跟《包法利夫人》非常相似,却远远没有后者有名。从留下的书信来看,福楼拜与她们都发生过争执,甚至最后分道扬镳。总之,《包法利夫人》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自福楼拜从身边女性汲取的灵感,但这些女性自身的写作却远没有达到福楼拜那样的成就。这是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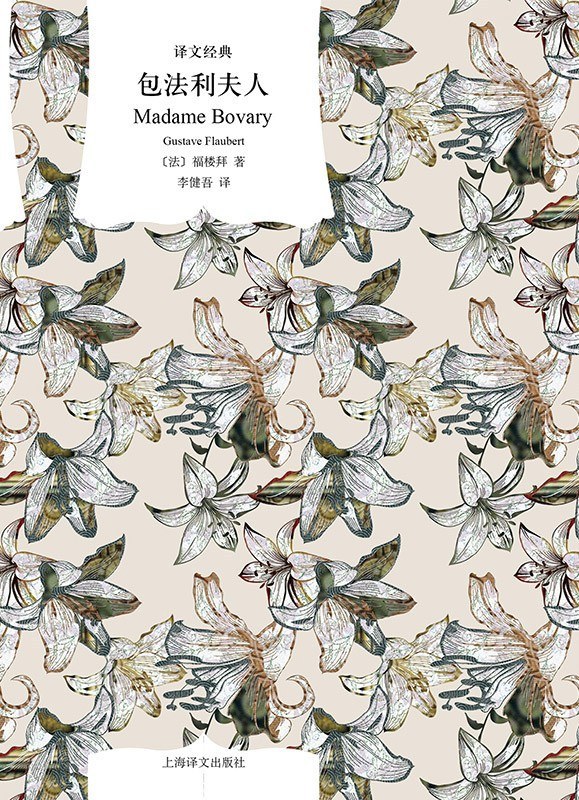
[法] 福楼拜 著 李健吾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7
张友发: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可作类比。有一次参加金鸡创投时,有位评委在讨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时提到过,建国之初,中国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电影的拍摄,甚至会让一些著名导演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然而他们始终觉得,到藏区采风后回来做电影,还是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奇怪感觉,直到很多年后,他看到藏族人自己拍的电影才明白自己缺失的东西——内生性视角。换言之,短暂采风是不够的,等电影教育和行业发展到一定成熟度之后,像万玛才旦这样的少数民族导演出现,汉族导演就不再替他们叙述自己的民族故事。
这和鹏凯说的“书写的权利”有所关联,不论是易卜生还是鲁迅,不是说他们真的能写出更好的女性作品或是更好地为女性发声,而是在当时的客观情况下,只有他们能够发声,鲁迅也曾在关于女性解放的演讲结束时坦言,“ 我没有研究过妇女问题,倘使必须我说几句,就只有这一点空话”,虽然是谦词,但也能反映一些问题。
徐鲁青:对,我觉得相比于问男作家能不能写好女性,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女作家会那么少,为什么文学史上都是男作家,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了女性写作?
比如伍尔夫就假设:如果莎士比亚有一位同样天赋异禀的妹妹朱迪斯,她的命运又会如何?在伍尔夫的笔下,朱迪斯可能会在哥哥施展才华的时候就自杀,如果她不自杀,那她的父母可能就会要求她本分地嫁人,剧院经理会将她视为笑话般挡在门口,最后只能流浪街头,也许一个好心的绅士会收留她,但也可能会在其怀孕后又丢弃。
乔治·艾略特就是化名男性发表作品,当时《呼啸山庄》在艾米莉·勃朗特被曝光是女性后备受争议,可见女性写作长期受压制。我觉得问题的核心不是身份/性别,一个好的作家是能深刻地共情他人、写出他人的,但作家能不能进入文学史,能不能被人看到,又由很多因素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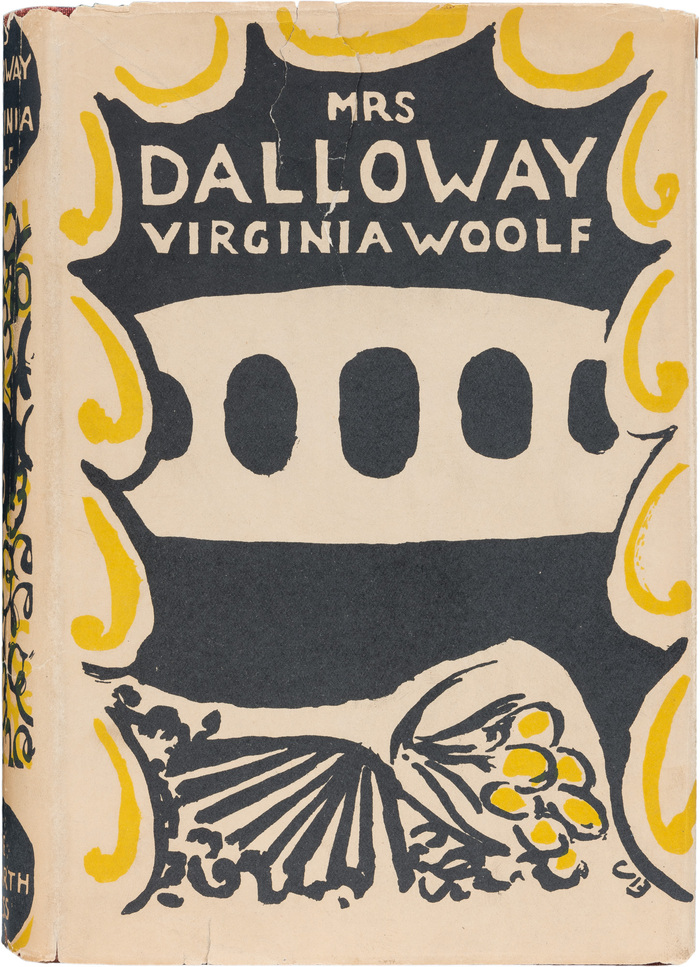
02 文艺作品是否真的与性别有关?
王鹏凯:前段时间谷雨发了一篇《跟王安忆一起寻找费兰特》的稿子,在猜测费兰特的身份时,王安忆坚称,费兰特只能是女性,因为只有女性才写得出莉拉和莱农,男人笔下是出不来这样的形象的。女性写作的视角是不是无法被替代的?或者说,它是不是有它的特殊性?
丁欣雨:陈丹青在谈《我的天才女友》时提到,作为一个快70岁的男性读者,他在看到许多异于个人经验的女性思绪和抒发后仍旧感到触动,甚至泪流,“等到小说家里有费兰特出现,我很感谢她,她告诉我女孩子是怎么想的,男人永远弄不清楚。”陈丹青说,在他过往的阅读里面,他不记得有谁能写女性写得如此深刻,所以女作家的出现确实会拓宽大家的阅读经验。
徐鲁青:提到费兰特,我想到她说过,女作家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个碎片,显然现在这条线还没有连贯起来。当我们想到俄国文学,很容易想到一些男作家的关系,例如托尔斯泰的思想又影响了哪些人。有些人会反对底层书单/外卖书单,又或者是各种身份建构出来的一些书单,因为他们认为无法将文学作如此分类,但我认为“全女书单”正巧是一种构建女性文学传统的方式,就像将这些碎片串联起来的线一样,把女作家的历史组成起来。

张友发:我们刚刚在讨论男性读者/作者与女性读者/作者的表达错位问题,其实从通俗文学的角度来观察,最近二十年是有一个分流出现的,通俗来说,就是分成男频和女频。网文是最考虑读者需求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它已经基本形成了两个互不交流、相对孤立的写作和阅读圈层:男频作者给男频读者写,女频作者给女频读者写。以男频为例,穿越类的、历史类的文章,读者会希望作者尽量不要写太多感情线,大火的小说还是在写,但基本上都是男性欲望的外化,因为不用考虑女性读者了,不会像现在的电影和文学这样,会担心有女性主义的批评。
这套秩序又因为改编逐渐蔓延到剧集领域,当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好几年前去采访一些制片人时,他们还在说“没有什么男频女频,只要大家爱看”。但慢慢地,大家已经意识到了,比如甜宠剧主要受众是女性,如果目标受众是男性,可能就要拍悬疑剧之类的,只不过现在剧集还没有像网文那样形成两个完全孤立的系统。
正如上周文化周报提到的,英国作家兼评论家裘德·库克(Jude Cook)创办了一家专注于男性作家的出版社,这会不会象征着一种趋势?这种趋势究竟是好还是不好?除通俗文学和剧集外,日本AV产业近十年也开始区分男性向和女性向,在人的欲望最直接,或者说读者需求最直接的部分,这种分流很明显,反而是纯文学以及电影还保留了很强的大众文化属性。因此,电影是最容易出现性别讨论的大中文领域,例如“为什么一个男导演要去拍女性故事”,女性拍的女性作品也会被一些男性拿来讨论。
03 内生性的视角是必须的吗?
王鹏凯:除了性别之外,其他身份也有类似状况,例如少数族裔或是残障身份,他们也都面临着在文艺作品被创作和代表的状况,这是否也与话语权力相关呢?
徐鲁青:残障权利运动最开始有一句口号叫作“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叙事),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呈现残障人士就需要残障人士的参与,那这和“呈现一个女性就需要女性的参与”是一回事吗?我感觉前者的需求好像更强一些,因为如果没有残障人士参与,健全人士很难理解残障人士的感受,进而有点像给残障人士做代言,但是我又会觉得,同样是两种身份,为什么男性和女性给我的感受就没有那么强烈?
王鹏凯:年初上映的香港电影《看我今天怎么说》,女主演钟雪莹作为健全人出演聋人,拿到了去年金马奖的最佳女演员,她在一篇专访中讲到,除了学习手语、与很多聋人交流外,她还有刻意地去关注和感受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种边缘的、失语的处境,这种处境也可以来自其他社会身份,包括身为女性,钟雪莹认为,这与聋人在社会当中的边缘感是相通的。

张友发:换句话说,我们四个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错位,当我们在讨论残障问题的时候,可能真的缺乏一个内生性视角,我们只能通过观看的文艺作品和身边接触到的人来讨论,但性别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丁欣雨:《独一无二》的原版《健听女孩》是由健全人执导的,影片选角时,三位听障角色均由真实听障演员出演。影片最让人感到冲击的场景也许是全家观看妹妹的音乐会演出,当妹妹在台上唱歌,镜头切换到听障父母和哥哥的视角——画面完全静音,只能看到父亲东张西望,在观察观众反应:有人交头接耳、有人流泪、有人鼓掌,他们什么也听不到。这段静音处理让很多观众惊呼,但我同时也在想,这种 “静音模拟” 是否依然是健全者对听障的想象性呢?因为很多观众一厢情愿地把他们的反应解读成是“紧张、不知所措”,进而有种同情的意味。
另一部听障题材电影《惠子,凝视》呈现了不同的创作思路。导演三宅唱在声音设计上刻意保留并放大日常环境音,如流水、车流、行人脚步声,而非采用静音处理来模拟听障体验。他在访谈中提到,许多作品试图通过 “静音” 营造 “共情假象”,但这本质上仍是健全人的主观想象,他认为,健全人在面对听障者时,往往先意识到自己“能听见”的特权,继而会刻意关注声音细节,因此,他选择如实呈现健全人视角下的环境音,让观众在“过度聆听”中意识到听障者与健全人之间的感知差异。这提供了另一种理解他人的方式。

徐鲁青:导演呈现的其实是自己作为健全人的感受,他只是如实记录自己的感知,而非揣测听障者的内心。我觉得这涉及两种创作逻辑的拉扯:一种是残障权利运动强调的 “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要谈论关于我们的叙事”;另一种是开头提到的,创作者应该试图通过自身视角去共情,哪怕这种共情存在天然局限。
张友发:我想到一个类似的例子,几年前刘涛出演了一部中年偶像剧,底层女性白手起家成为高管的故事,剧情非常狗血,豆瓣也被打了非常低的分数,但最后大家惊讶地发现这部剧收视率很高,中老年人非常爱看。当时有记者问妈妈为什么爱看,不觉得这部剧很假吗,但妈妈说故事很有趣,而正午阳光的年代剧反而“太真实了,我们都经历过,有什么好看的”。
这让我有一种错位感,当我们无法共情另一个群体时,叙述往往容易陷入两种模式:一种是猎奇式表达,使其成为被凝视的 “他者”;另一种则是 “善意的越界”,即用主流价值观替边缘群体发声,例如为中老年群体创作的剧集,创作者往往预设他们 “应该” 关注历史苦难或严肃议题,但现实中可能他们就是爱看假靳东,喜欢给秀才打赏。所以得让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或者有内生性的视角和选择权,甚至我觉得都不是表达的自主权,而是评论的自主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听到不是这个群体的人的评价。
04 讨论身份政治之后
张友发:如果身份意味着一种结构,那身份转变的背后意味着新的视角、新的可能性。举例而言,女导演和男导演的拍摄只是性别转化吗?还是说会带来整个体系的变化?
今年邵艺辉有一篇采访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提到她的一些指导方式和原本的片场“不一样”。比如片场的群头是很凶的,呵斥群演的时候会让她感觉到恐惧,甚至有点反感,于是她会请男性工作人员提醒这个群头。此外在传统的电影体系里,男性凝结团队的方式就是喝大酒,而邵艺辉主动避开了带有社交性质的饭局,她担心自己能不能凝结团队,制片人叶婷说了句挺有启发性的话:“你用烟酒打开他们,那就是烟酒的方式。你用职业工作的这种方式打开,他就是给你呈现这一面。”这带来的其实是片场权力结构的变化,如果有一个女性导演,她还是用男性导演的方式去拍片,呵斥、酒局,只是让自己变成这个体系里面的一个男性,那这个解放性肯定是有限的。

徐鲁青:有一个残障设计师也跟我说,其实现在很多残障设计或者无障碍设计,大多是健全人“需要”的。但是当足够多的盲人设计师或聋人设计师进入到这个行业,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去考虑残障人士是怎么使用耳机的,这是身份转变带来的更大的结构上的改变。
同时,我们现在讨论身份表达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国谈和在美国谈是特别不一样的,因为美国已经谈了非常非常久,但是在中国可能才刚刚开始谈。我们才刚刚开始做全女书单,才开始说女作家,大家才开始注意到我们有这个身份存在,女性写作和男性写作是不一样的,等等。如果真的要去解决更多问题,比如要去拍一个残障的电影,要有更多残障的电影出来,但问题是没有那么多残障演员,那是不是在大学招生的时候需要有更多残障的名额?或者是一个残障小孩,他在选择自己的专业或者未来的路径时可以去做一个演员,而不只是说读盲校,然后进入社会给予残障人士专门的就业岗位。我觉得上述提到的是更大范围的改变,而现在只是在最开始的阶段。
王鹏凯:我接着鲁青的话题往下聊。当下女性、弱势群体在发声后如何往下走,其实这个问题在西方尤为明显,少数族群在获得创作机会后往往会面临新的困境:你只能写跟自己身份相关的主题。我之前听越南裔美国作家王鸥行的一期访谈,他说自己的第一部的小说《大地上我们转瞬即逝的绚烂》最初被很多出版商拒稿,因为他的故事里主题太多了,例如同性题材、越南记忆和亚裔身份认同,有人建议他专注写移民故事就可以。从今天来看,当这些弱势群体得到发声机会以后,他们很可能会陷入这种“只能写自己身份故事”的限制。
但与此同时,这样的困境也带来了一种张力。美国评论家朱华敏(Andrea Long Chu)在一篇有关女作家蕾切尔·卡斯克的文章里提出了在我看来很值得思考的批评。卡斯克认为,需要警惕男女平等后对男女价值观的混淆,女性应该正视自己性别内部的奥秘和悲剧,在她看来,一本书并不会因为出自女性之手就成为女性写作,只有当它无法由男性写出时,才真正成为女性写作,例如有关成为母亲的作品。但朱华敏很直接地提出反对,认为这无异于“将空气定义为男性,并自豪地拒绝呼吸”,在朱华敏看来,真正的挑战并不是当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所有优势后,能否创作出同等水平的作品,而在于她们在获得这些优势后,是否能不再被视为“女人”。换言之,当女性获得跟男性一样的权利以后,是否存在新的创作可能性?